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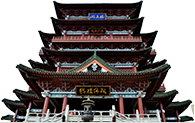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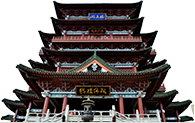
如洪水猛兽般袭来的疫情,打破了所有人心中关于2020年的新年计划,更是对整个国家予以了一击重创。
在封城期间,屡屡在网络上看到企业诉苦类文章,比如海底捞日亏8000万、西贝撑不过三个月……当时内心还有所庆幸,律师行业虽然是服务行业,消耗成本相对是很有限的。比如我所在的律所便不存在办公室租金部分的支出。
但是总体来说,2020年的第一季度,我这样一个身处小城的刑辩律师状态是维系旧业务,难拓新业务。
所以,即便是0成本,面对0业务亦难堪承受。
在二月份,最严格的疫情管控期间曾写过一篇《后疫情时代下的小城刑辩律师》,是关于疫情解控之后小城刑辩工作开展的预想,也谈了谈自己的生活状态。
如今过去了近两月,疫情管控在逐渐放松之后又因全球疫情蔓延又在稍稍收拢抓紧。小城刑辩律师的工作模式从当时的居家看书、远程听课、电话沟通的方式转变为正常的行政上班、未开庭案件案头工作的正常办理,同时继续远程听课。
在律所内,已经可以看到民商事律师如火如荼地重新步入工作的正轨,但是自己手头上的刑辩工作因会见、开庭的困难,而被迫半复工,甚至未复工。所以,小城刑辩律师在疫情稍解控的今天,依旧还是需要自己“找乐子”。
前两日重读《法律人的明天会怎样》,书中有段话,“说到这里,律师还值得吸取比“颠覆”问题更大的教训:永远不要忽视接受你们服务的人。当你们律师考虑某种创新的时候,多站在你们试图帮助的客户的立场来考虑。你们的创新对他们意味着什么?”今天就想聊聊自己的思考。
在刑辩领域,工作内容上没有太多创新的空间,按着诉讼程序都得走在阅卷、会见、开庭的轨道上。有关如何快速有效阅卷、怎样辅导好当事人的会见、何以最佳表现的开庭等等提升工作效率的方法论讨论得比较多。所以,在看到此段话时,我想换一个方式问自己:辩护方案的选择,对当事人而言意味着什么?
“客户思维”这句词语,我在近一两年多个地方多次听到。要想钓到鱼,就得像鱼一样思考。要把东西卖给客户,就得知道客户在想什么,需要什么。电影《华尔街之狼》中有个很经典的桥段“你来试试把这支笔卖给我”,失败的经验是仅仅强调笔的好处。而成功的经验是为客户提供需要使用笔的理由,也就是为客户创造需求。
“独立辩护权”,在2017年全国律协通过的《律师办理刑事案件规范》中表述“律师担任辩护人,依法独立履行辩护职责。律师在辩护活动中,应当在法律和事实的基础上尊重当事人意见,按照有利于当事人的原则开展工作。不得违背当事人的意愿提出不利于当事人的辩护意见。”也就是说,律师辩护权的基础是当事人的委托,不能不顾当事人的意志,只顾自己的“形式表演”。在尊重当事人意志的基础之上,最大限度地维护当事人的利益,是辩护工作的第一原则。
辩护方案的选择,最终通向的道路是为了当事人利益的最大化。律师基于自己的专业判断,对案件辩护方向会有更深层次的思考。
但站在当事人的角度,则会因人而异。有一些不愿意去过多纠缠案件证据问题,只想程序走快点,早日判决、早日服刑、早日出狱;有一些不愿意面对事实、证据,避重就轻,只关注案件中细枝末节的小毛病力争脱罪、罪轻;有一些只是不信任法律,怀疑辩护效果,宁愿找关系;还有一些没有任何想法,律师说什么就是什么……
“客户思维”与“独立辩护权”两个概念,一般看来是风马牛不相及。“客户思维”是商事领域的销售技巧,在律师工作中似乎更像是如何成功接受委托。“独立辩护权”是委托之后的工作理念。但我认为,在辩护方案的选择中,两者是有相通点的。两者都须基于当事人/客户的需求,或者说当事人/客户的最大利益,这是我们工作的出发点。在与之沟通的过程中要进行协商,将自己的思考和建议传达给当事人,将当事人的要求再融汇进自己的辩护思考中。
“律师画地图,当事人来选择”,辩护方案的选择并不是一道简单的、固定的选择题,是会在沟通过程中、案件进程中不断调整的。我们会逐渐理解当事人内心中的固执,当事人也会逐渐领会法律后果对自身的意义。
现在碰到比较多的情况是,在审查起诉阶段当事人会问律师意见,“我要不要做认罪认罚?你帮我分析分析……”我们通常会根据案件证据情况、量刑幅度等与当事人逐一说明,同时给出建议。类似证据确凿,当事人无异议的案件自不必说,会明确建议当事人作认罪认罚;案件定性存在较大争议的,当事人坚持无罪抗辩的,也无需多言,会直接遵从当事人意愿,不作认罪认罚。
而需要与当事人多次协商的,是事实没问题但定罪有难度的案件。例如,有些案件在犯罪事实上有供述、证人证言等证据证实,系事实无异议,但罪名的定罪量刑还须其他如鉴定意见等证据,但这部分证据尚未完全确凿,系定罪有难度。这个时候会出现一个选择,“协商还是进攻”?
进攻型辩护,是在与检察机关沟通无效后,待案件诉至法院开庭审理,将证据问题一并提出,可谓是“较真了”。协商型辩护,是与检察机关进行谈判,对存疑证据“大家各退一步”,为当事人的量刑争取一个更好的结果。两种方向的选择,会带来不一样的结果,结果的承受者都是当事人本身。所以,作为律师无法仅凭个人意愿,比如想在庭审上酣畅淋漓地“斗”一场,还是简单、快速地一场庭审来建议当事人。
也有人评论说,律师都巴不得给当事人做认罪认罚,这样后面开庭就没事了。这种观点,我是非常反对的。某些案件本身事实无争议、案情简单,程序是可以走的很快。但有些案件,就比如我上述提到这种事实无异议、定罪有难度的,如果做了认罪认罚,的确庭审节奏会快很多,但那是因为律师已经把主要的工作在审查起诉阶段完成了,是问题处理的前置化。这个阶段选择认罪认罚,与检察院的沟通从工作量来看不会比庭审准备少,甚至殚精竭虑的还会更多。
“独立辩护权”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,基本有了定论。但是换一种方式问问自己,“辩护方案的选择,对当事人而言意味着什么?”这虽然包含了“独立辩护权”的问题,但我认为这不失为一种换位思考的尝试。
(来源:江西盛义律师事务所)


